之前听过一个说法:当感到有人正与你为敌,不如想想,三百年以后,你们在哪里。
一直觉得这句劝人放下愤怒的静思语虽然立意良善,但充满陷阱。
只要人活着的一天,就无法放下存在,于是去想三百年以后,也只是为了改变、珍惜或缓解当下的感觉,甚至影响当下的决定。于是看着这句话,我倒也想不到以后,而是想着,除了现在以外,我无法在任何地方,逃不走也避不掉。
三百年,是个抓得满准的数字。三十岁,你生了小孩,孩子在你六十岁时又生了小孩,孙子在你九十岁时也生了小孩,他们指着照片跟自己的小孩、跟他们的孙子说:你看,这是你祖父、曾祖父、曾曾祖父......他们去你的墓前上香。但过了三百年,有很大机会所有爱过你的人、知道你名字的人都死光了,不再被记得,真正意义上的死亡。
《鬼魅浮生》是导演大卫·洛维致敬作家吴尔芙的短篇小说《鬼屋》的作品。
吴尔芙的鬼魂没有形体,一对鬼魂,在一对活人居住的家屋中穿梭,在门廊间关门、又开门,试图记起自己究竟曾经在找什么、在做什么,试图在由活着的身体所累积的记忆当中延续生命。
电影中,如风的鬼魂则成为一个套着白色床单的人物,以半梦半醒的意识经历这种百年的孤单。导演罗利说,最初他只是有个想法,要拍一部电影,主角就要是那么一位套着床单的鬼魂,看似戏谑,却让吴尔芙的意识流书写有了一层皮肤。
床单作为中介,让鬼魂看似可以碰触,却又总是隔着一层距离;让他几乎可见于活人的视线,却又没有共同的形貌,天人永隔的无奈于是透过亲密被凸显了。
展开全文
亲密是爱人之间的关系。吴尔芙所并置的活人情侣与鬼魂情侣,在电影中融合为同一对佳偶。
小说中生与死这组对立概念之互换,是当鬼魂看着熟睡的活人,谁是生谁是死?而电影中则以角色展现。他们也住在一个充满历史的屋子里,女人想搬家,男人却想留下。
争议告一段落,他们决定走,男人却在此时因故去世。化为鬼魂,隔着床单,他试图安抚悲伤的女人,在女人感到最寂寞之际,他就在她身后几公分的距离。
他看着她哭着睡了一觉、洗了澡、洗了床单,洗去他的身体曾经留下的味道。
屋子在吴尔芙的小说里也是重点。
宝藏是什么呢?宝藏是两个鬼魂对彼此诉说的共同回忆。
在电影中,宝藏转化成一张小小的、藏在门框缝隙里的纸条。
开场,女主角因为一股害怕的情绪笑了,她不知道她为什么害怕。她开始说,小时候,每次搬家,她都会在旧房子里留下一张纸条,那上面写着她想记得的、关于那座房子的事物,那就像是将家的归属化为一些字句。
屋子与其中的人栖居于字句当中,包括一部分的她自己,永远安全。
究竟女主角怕的是什么呢,是死亡吗?
死亡是从一个状态转换到下一个状态的交叉点,像换工作、搬家,像离开一段关系或离开一个城市。
在经历转变时,我们产生无以名状的情感,近似恐惧,又有点刺激,就像在一阵忙乱之后,旅人上飞机、上邮轮、上巴士,在自己的座位上,一阵突如其来的安详中,升起某种自己即将死亡的预感。
我们在生命中的每一次转变都感到失去,我们不解事情为什么一定要是这样子,是谁夺走了转变以前、我们曾拥有的那些东西呢?
如果说我们执意要害怕死亡,那为什么不在每分每秒这样细致的格局去害怕?为什么我们如此放心地让一个个细胞死去、让八点五十分变成八点五十一分,而不大惊小怪?
因为我们不害怕在这一分钟之内我们会有什么改变,或者,再害怕,也总是会过去的,但死亡的那一分钟却可能为现下的状态带来全盘的改变。
“死亡是敌人,我将坚定而不屈服地把自己朝你扔去。海朝岸上涌去、碎成浪花;死亡是敌人。我要与你对抗,坚定不移,坚定不移地死!波浪在岸上爆发了。”
这是吴尔芙的丈夫为她挑选的墓志铭,出自她的小说《海浪》。
在小说的最后,他似乎意识到第一人称的谎言,意识到自我意识永远无法不与他者混同,而眼前所见的熟悉环境中,又是一个一如既往的一天。
在这样的周而复始里,他看见了永恒的无限延长与重复。此时,他向已经这么熟悉的海滩说出了以上那段话。这是吴尔芙对死亡的清晰体悟,它的本质是改变。
但清晰也总是会恐惧,1934年她的挚友罗杰·艾略特·弗莱心脏病发死亡时,吴尔芙也曾在日记中写下对死亡的恐惧,即使恐惧,她最后也众所周知地,坚强而不屈服地将自己朝家里附近的乌兹河中扔去。
可是在鬼魂流连的房屋之中,吴尔芙写的不只是死亡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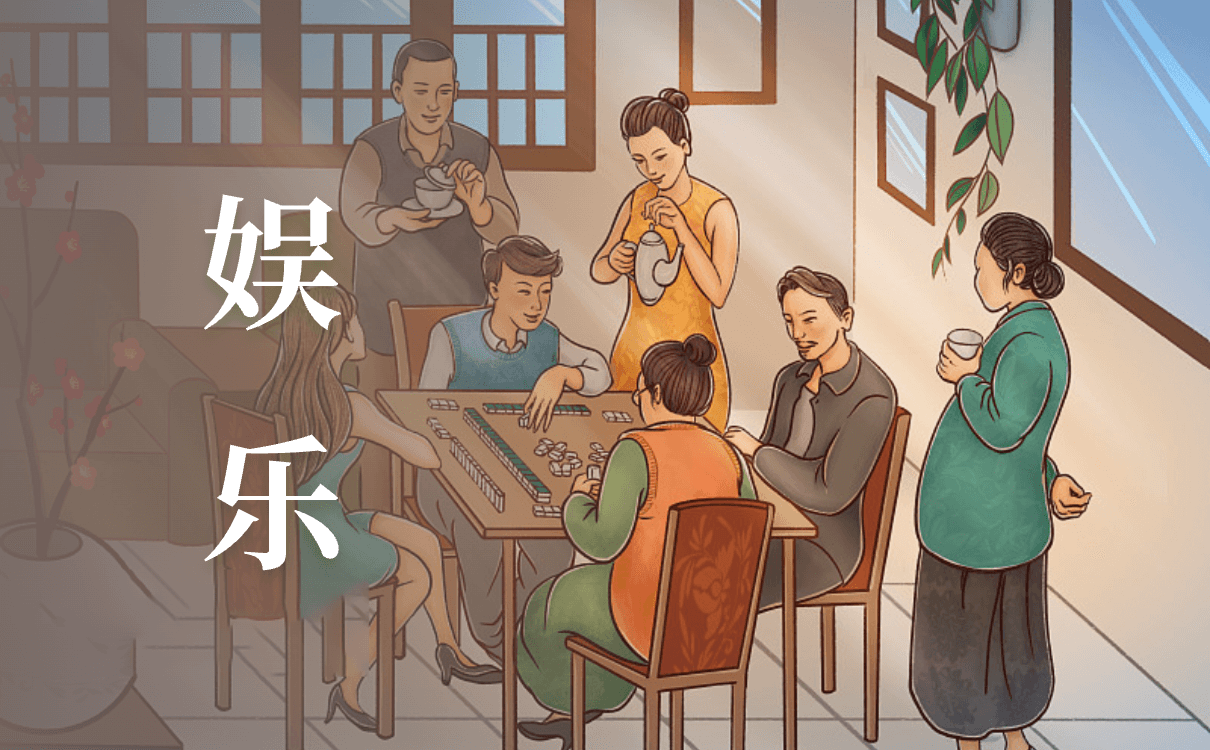
她写——Deathistheglass。除了在房屋里乱窜的风,还有光线进入的窗户,玻璃上映照的是什么呢?《鬼魅浮生》中随处可见光影,在墙上、在活人身上。所有的光影,不管有心还无意,都是鬼魂存在的证明,那让死亡展现了反射生命之光的意象。
在极简的情节里,导演也试图让十九世纪的文字有了更现代的诠释,也更能唤起21世纪的人们心中的寂寞。
男主角的职业是音乐家,透过流行歌歌词,导演指出了鬼魂的另一种无处不在。
在发光的萤幕之间,恋人消失了,好像只要不眼睁睁盯着,身边的人也会随时消失。男主角透过这歌词向女主角表达消失的恐惧。死亡于是的确刻刻与我们随行,以存在之缺乏形式。
在女主角搬走后,一位单亲妈妈跟两个小孩子住了进来,鬼魂摔碎了家中物品,企图要展现自己的存在,却徒劳无功,一个经典闹鬼场景,却也是我们向重要他人索取目光时所感受到的无助。
又一次的时过境迁,屋子里的派对场景,众声喧哗之下,这座「闹鬼的房屋」中再也没有人看得见、听得见鬼魂了。
一位厌世文青将手中的空啤酒罐一丢,开始对贝多芬发表长篇大论。与整部片的宁静和抽离的视角放在一起,这段独白像是将观众从诗意想象里拉回现实。
事实上,在总共五页的剧本台词中,它就占了四页。我认为这是很聪明的选择,毕竟看完一部关于死亡的哲学电影、或读完一篇吴尔芙后,人们还是得回到日常生活,而大部分的日常中没有鬼魂,只有人们酒后的长篇大论。
厌世文青到底嘴了贝多芬什么呢?帕斯捷尔纳克的长篇小说中的一段《齐瓦哥医生》书中的段落大概是个很好的注解:
什么是历史?它是人类数世纪以来对死亡之谜有系统的探索,对征服死亡的期待;它是人类发现数学的无限大和电磁波的原因,也是人们谱写交响曲的理由。
文青说着,不知道多少年以后,历史毁灭了人类文明,一群仅剩的人跑到洞穴里生活,觉得人类差不多要完蛋时,有人哼起了贝多芬《第九交响曲》,已经没有人知道贝多芬是谁,但这曲子让人类想要继续下去。
不过,再怎么继续下去也有终点,因为宇宙还是会不停在膨胀与收缩之间往复摧毁与创造生命。所以你要写交响乐、要写书、要盖房子要干嘛都可以,但别幻想那是一个可以让你在死后留下什么的希望。
这不过是虚无主义的持续延伸与变形,却也是我们这代人的某种生活代表。导演将人类试图留下各种遗迹以对抗死亡的意志说得很清楚,也许太清楚了,少了吴尔芙的“空”,却是属于我们这时代的厌世。
我们理解了宇宙大爆炸,从事实的层面理解了所有事物都要消亡,但难题还是一样。
怕自己曾经的遗迹消失,即使多微不足道。
但那种“拥有”遗迹的想望可以更广阔。鬼魂穿越时空回到房子盖起来之前的时代,一个十九世纪的小女孩在哼唱他写的歌,她也留下一个小纸条在石头底下。
吴尔芙写的宝藏,导演透过电影想回答的:我们需要什么,来在人生中继续走下去。
导演说了一个鬼故事,意在带给观众平静。但平静或许就是此片的恐怖之处。
平静是要懂得如何当一只鬼魂,不过鬼又是什么呢?电影开头也是吴尔芙小说的第一句话:不管何时醒来,总有一扇门正关上。
这个意象包含了声音、动态、肉眼不见的风。因为看不见,所以你永远可以说那只是风。
